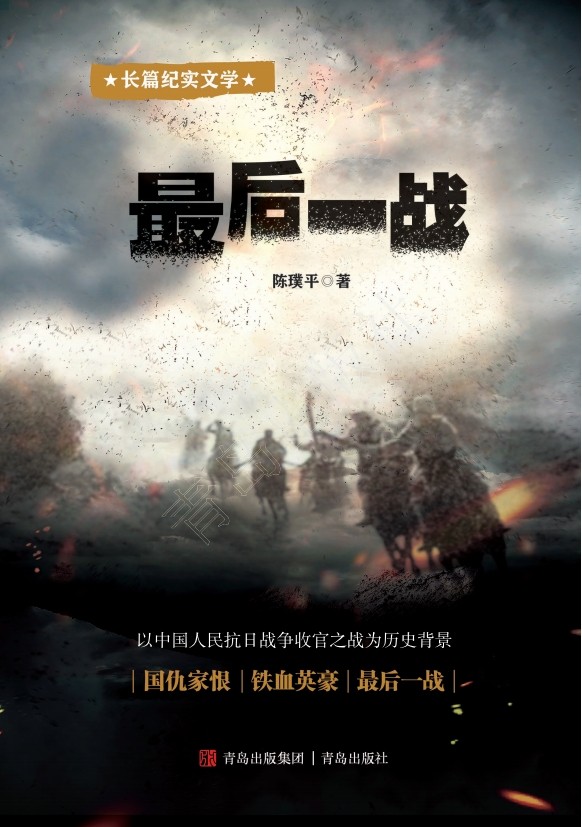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其后少数未被消灭的日本侵略者仍负隅顽抗。1945年12月27日——31日,我山东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冀鲁豫部队、平禹县大队、齐禹县大队的配合下,向日、伪、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禹城大战。此战不仅是山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而且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收官之战。
为了再现这场鲜为人知的抗日最后一战,德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德州市党史专家库总顾问陈璞平寻访禹城大战目击者、参战者及参战将领后代,广泛查阅有关抗战历史文献,精心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最后一战》。以气势恢宏的笔墨,全景式展现了禹城乃至鲁西北人民的抗战历史,特别是对禹城大战的真实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立体的展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2月5日起,奏嘛新闻客户端推出长篇纪实文学《最后一战》连载,敬请收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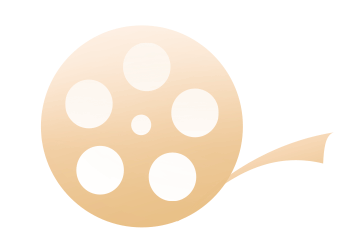
我站在徒骇河畔,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历史就如同这波涛汹涌的大河,经历了多少暴风骤雨、惊涛骇浪,只为了永不停歇,奔腾向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鉴往知来,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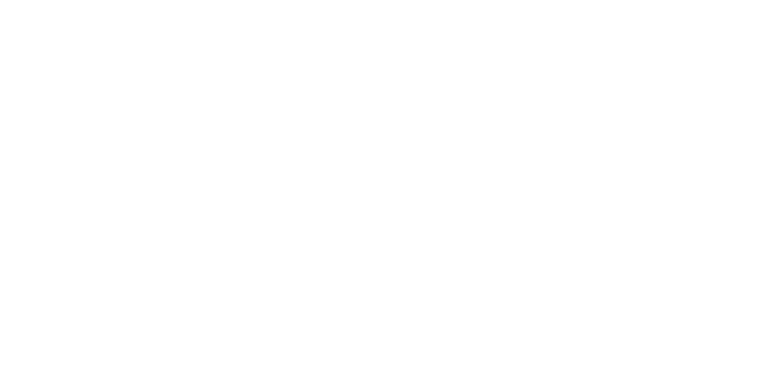
2021年仲夏的那个夜晚,我一口气讲完四子的传奇故事,已是夜半三更,节目组的成员却回味犹酣,意犹未尽,半天,屋内没有一丝声响。
许久,才有人询问四子后来的情况。
我说:“禹城大战结束后,有人反映,四子刺杀小野的最后一刀是在山谷宣布投降之后,属于公报私仇,虐杀俘虏,违反了军纪。于是,上级派人前来调查,折腾了半天,也没弄清那小野到底该不该杀,最后以擅自行动为由给他一个军纪处分,此事总算不了了之。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军区特务一团先是编入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改编为第28师第82团,后又改编为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1947年8月,已经担任副连长的四子在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梁山阻击战中身负重伤,送回惠民后方医院治疗。在此期间,饶漱石、康生在渤海区推行‘左’倾政策,以景晓村为代表的一大批老渤海干部被撤职,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四子当时也被以历史不清为由强制复员,回乡务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因为渤海区事件受牵连的干部陆续平反,他也找组织反映过个人问题,可上面说,他是因伤复员,并不属于遭受迫害范围,自然也就不存在平反昭雪问题。好在四子对名利向来看得淡,从此便再未向上反映。”
又有人追问:“在这之后呢?”
我摇摇头道:“在这后来,他来找我父亲时,对我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再后来,我考取大学离开了家乡;再再后来,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从此便和他失去了联系。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他到底属于连五高的哪个村。但是,在我心里,他已经演化成鲁北人民抗战记忆中的一个概念、 一个符号。在禹城,在鲁西北,在齐鲁大地,像他这样的无名抗日英雄数也数不清,像他这样的传奇故事讲也讲不完。”
第二天清晨,节目组人员回京,临走时娟子一再叮嘱我,如果找到四子,一定告诉他们。
四子生于1924年,属鼠,2021年97岁,大概率应该不在人世了。
但是,我不甘心,怀揣着一丝希望依然在努力寻找。
2021年秋,《揭秘禹城大战》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引起强烈反响,我也因为客串嘉宾主持过了一把电视瘾。
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中日最后一战”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上面,这是我酝酿多年的创作梦想。在连五高、东玉皇陈、东唐、达子等地,在鲁西北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我听到了一个又一个闻所未闻的抗日逸事,但就是没有四子的任何信息。他就像一阵轻风、一粒尘埃,在宇宙间彻底消失。找不到四子,成为我至今无法打开的心结。
为了撰写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我收集了上千册历史资料,手写了多达上百万字的采访笔记,敲打下数百万字的电脑文字。但是,最初一段时间,我很迷茫,太多太多的原始资料和奇闻轶事堆积在面前,以至于有些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取舍、从何下笔。那些日子,我苦苦思考:这部作品究竟应该写什么?是四子的悲苦恋情、复仇传奇?还是徒骇河畔的市井人文、逸事趣闻?或是日寇的惨无人道、滔天罪行?抑或是鲁西北军民的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直到读了日本右翼分子近藤宏书中的一段话,我才真正坚定了写作的重点和方向。
近藤宏在书中回顾了当年日军兵败禹城经过之后,这样说道:
经过漫长的岁月,大东亚战争也大多埋没在过去,即将被人遗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陈家庄的村子里勇敢地发起冲锋,然后又勇敢地牺牲的小林小队,以及在铁路周边壮烈殉国的将士们。在中国的山野中,还有许多英灵至今不能回到日本,也不能安息。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各地,像禹城战役那样悲惨地结束的许多战友和同胞,不能让他们无缘于中国的山野。战后37年(该书出版于1982年 — — 引者注),这种想法至今历历在目。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用自己的手来祭奠死去的战友,这也是所有活着的战友的迫切愿望。(近藤宏:《重庆攻击队》,东北新闻社1982年日文版,第210页。)
读着这段赤裸裸、血淋淋、咬牙切齿、阴魂不散、通篇散发着军国主义腐臭的字句,我突然明白了我究竟应该写什么。侵略者在时时刻刻提醒他们的后人,不能忘记那场远逝的侵略战争;我们作为曾经的受害者,又怎能将它轻易抹杀和遗忘?
2022年仲春,我再次来到徒骇河畔,目睹当年鲁西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遗址,眺望滚滚东去的河水,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历史就如同这波涛汹涌的大河,经历了多次暴风骤雨、惊涛骇浪,只为了向前,向前,永不停歇,奔腾向前!
面对滚滚洪流,我豁然开朗:我们无法改变历史,能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鉴往知来,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抬头望一眼天空,那个模糊的身影在浑浊的记忆深处向我走来,慢慢地,所有的一切似乎越来越清晰。我突然感到羞愧,这么多年过去,我竟然将他从记忆中祛除得如此干净。(点击观看)
肖锋旅长说:“就在最近几天,日军渡边师团131联队山谷大队千余名鬼子进驻禹城火车站,企图在此负隅顽抗。这股日军就像扎在我解放区胸膛上的一根毒刺,若不及时将其拔出,必将后患无穷。”(点击观看)
爆破手们逐个清除碉堡。火光中,一座座碉堡前跃动着抱着炸药包的身影,轻重机枪刮风似的叫,炸药包“轰隆隆”震天动地。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再上;再倒,再上。小碉堡终于被全部清除。(点击观看)
嘹亮的冲锋号在空旷的田野上空回荡,我军战士以班、组为单位,似股股旋风卷了出去,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坚毅的杀气,咬着牙、瞪着眼、呐喊着、咒骂着向前猛冲。(点击观看)
第十
二章 合 围
第十三
章 格 杀
第十四
章 落 幕
第十五
章 铭 史

陈璞平,祖籍山东禹城,196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山东省德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德州市党史专家库总顾问。酷爱党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有《迷航—1927陈独秀在武汉》《陈独秀之死》《母亲的红色之恋》《无字碑》《兵出渤海湾》《西风烈》《将军泪》《渤海女兵西征记》《乱世兄妹》等多部著作,尤其擅长撰写军事和历史题材作品,享有“红色作家”之称。作品曾荣获4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等多项国家、省、市作品奖。
打开“奏嘛新闻”看评论